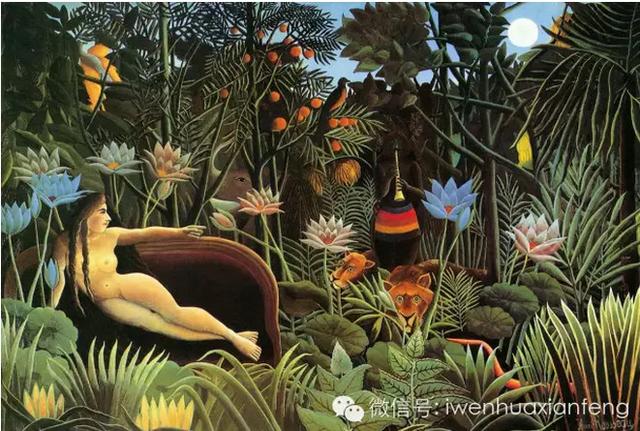
格言化使诗歌与大众越来越近 但难度也在下降
徐鹏远:非常感谢诸位参加2015上海诗歌艺术节凤凰文化读书专场讲座,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朱大可和欧阳江河两位老师带来一场对谈,主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大众更需要诗歌?”闲言少叙,首先我想替在座的观众盘问一下大可老师,即便有读者读过您的诗歌评论,但您的标签基本还是一个文化评论家,您写过诗吗?
朱大可:基本没写过,但也有人认为我用诗歌来写我自己其他的文字,称作是“诗性写作”。我觉得诗歌也好,其他文字也好,内在的原则是一致的,其实就是隐喻,隐喻是诗歌的基本手法,也是我使用的主要写作方式。
徐鹏远:那您觉得从事诗歌评论,和从事大众文化评论的区别在于哪里?还是说两者其实在您看来,它使用的基本方法、包括我们所关注的角度等等,是相通的?
朱大可:我做的批评有很多的工具,有些工具是适用于诗歌的,有些工具不适用于诗歌,所以还是有些区别。但是因为工具较多,就像手术室工具盘里的大量工具,进展到手术的某个阶段,就需要更换另一种工具,工具越多,使用起来就会越方便。
徐鹏远:今天题目里其实埋了好几个陷阱,“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大众更需要诗歌”,第一个陷阱就是当我们把诗歌和大众并列放在一个标题的时候,潜台词是诗歌和大众本来是分野的。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这个问题各自有怎样的看法?
朱大可:我们先来看诗歌的出生证,就“诗”这个字而言,首先它跟寺庙有关系,它是寺庙里的言说,所以它就具有天然的神性。最近大众谈论的话题是《芈月传》是吧?这个“芈”字很多人读不来。芈是什么意思?芈就是楚国当年的祭司,全世界的祭司都来自波斯,世界上凡是跟祭祀有关系的祭司和巫师,这些人的名字都是M打头的。举个例子,汉字里巫师的巫,古音是ma。屈原他老人家姓什么?芈。他应该叫芈屈原。现在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楚国的大祭司,祭祀的时候要用诗歌唱诵,以此来跟神灵交流。这就是所谓诗歌的起源。
现在我们把屈原身上宗教这部分加以剥离,把他看作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实际是把他的神性阉割掉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诗歌的神性。但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诗歌却在不断地跟它的神性告别,到了今天,我们只能听到这样的诗句——“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通过这种句式,诗歌跟大众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而跟神性越来越远。
建构大众跟诗歌关联性的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方式,那就是把诗歌格言化。比如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散文家胡兰成也说,“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另外,你还能看到汪国真同志所制造的大量伪格言,这些东西都在让诗歌难度下降,也就与大众的关系越来越近。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诗歌节”,可是我想请教大家,歌在哪里?我们的庆典里有歌吗?所以严格来说,这只能叫做“诗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歌推开呢?因为人们通常以为,歌是属于音乐界的东西,但问题就在于,音乐界也不承认写词的属于音乐界。音乐界的大佬们甚至认为歌曲也不是音乐。其实歌是诗与大众之间的最好的中介,可是因为两边都不相认,它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尴尬。
诗歌是世界上唯一还能保持痛感的东西
欧阳江河:刚才大可追溯了诗歌的出生证。如果追根溯源,从字源学的角度来讲诗歌一开始就注定了它跟神性的关系,但是整个诗歌的历史,诗人的角色演变、成长转化的历史是神性的东西越来越远、离“巫”的东西越来越远。而且不光是诗的意义,也从声音的角度,歌的成份被慢慢去掉了、弱化掉了。
按照大可老师的梳理,诗歌慢慢变成一方面可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因为它可以交流,可以励志,可以引起共鸣。像汪国真和余秀华这种能不能被称为诗歌?宽泛地来讲是可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诗歌诗态各种各样,对诗歌本身的需要就是多元的。这个需要的后面是不是隐藏着一种阅读意义上的消费的冲动?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物质基础得到了满足和释放,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不是感到了心灵的荒芜,这个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诗歌最能够排解这种精神的空虚和荒凉,最能够给人安慰和慰藉。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诗人,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诗歌的消费需求和冲动,或者是交往意义上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从我自己来讲,我的写作不是这种需要制造出来的,不是为了满足这种意义的,比如说对美的要求、对格言的需要、对交流和心灵慰藉的需要、对孤独的需要,我的诗不接受这种意义上的需要的订货。
每一个诗人都会在心里有他的理想读者,决定写作的命运。我的理想读者是一群幽灵读者:李白、杜甫、荷尔德林、庞德和荷马。我没有按照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样子去写作,但是我把他们预设为我的理想读者。我老在想象他们会不会挣开眼睛,来读我的诗,会不会看一眼就走了,说你这叫诗吗?还配给我读吗?这就是我的,对于来自阅读的那种绝对标准。我的幽灵读者还包含三百年以后的人,包含火星上的读者,我的诗能经得起他们的阅读吗?这是我说的同时代,包涵未来和过去,各个时代在我的身上,同时被唤醒、同时发生、同时活着,同时阅读我写的诗,我能满足这种阅读要求吗,我敢接受这个委任状吗?
于是我的写作可能里面就预设了一些疯狂的东西,有力学的崇高,有数学的崇高,把对宇宙的根本看法,把宇宙观、世界观的东西放到我的日常生活。我今天跟大可还在讲,我说为什么上海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干脆写得烂一点、写得差一点、写得羞愧一点,但是能像豹子一样抓我一下,而不是像猫的舌头舔我一下的诗人?痛感在哪里?狠劲儿在哪里?上海那些写好诗的诗人,能不能把上海现实中间的狠的那一面,罪恶的那一面,羞愧的那一面,失望的那一面,不能被消费的那一面,不甜的那一面写出来?当我们用这种胸怀把上海复杂、混乱、残忍一起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会不会是对之前我们所说的优美诗歌的冒犯?如果是冒犯,你能容纳吗?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呼吁的是写作和阅读双重意义上的原创性以及它的真实性,不能只从消费的角度理解诗,理解大众们对诗歌的需要。
30年转型让我们的诗歌软绵绵或者幻觉崇高
欧阳江河:刚才大可讲得非常全面,涉及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比如他讲到,在灾难的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可能出大诗人,愤怒出大诗人,或者就是像上海这样的多元碰撞出诗人。我在想“911”之后,几乎整个纽约的人全都开始读诗,这种对诗歌的需要,我不能说它是一种消费性质,而是一种在宗教里都寻求不到的解脱和安慰的时候的需要。在当代,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海子。大概在1990年冬天的时候,有一天重庆大学诗社的社长来找我,说他们学校一共一万二千人左右,中秋节那天晚上,大家集体朗诵海子的《秋》,“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后来他们认真统计了,有9000个人在那一瞬间全部是背诵的,也就是说一万二千个人里面有九千个人会背诵海子的诗,真是一个壮举。
朱大可:诗歌大众化有一个途径,只要进了课本你就是大众诗人了。大家都应该知道,舒婷有好几首诗都成为中学教材,于是乎他们告诉我,舒婷在宁夏银川的万人体育馆朗诵她的诗歌,底下的观众就跟看到刘德华一样卷入狂欢,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人就是舒婷,这可能是一个孤例,我想补充一下。
欧阳江河:当然也不是说进了中学课本就有可能享受大众狂热追捧的待遇,我有一首诗进了中学课本。我知道大学学哲学的人,特别喜欢我这首诗,但是你把它放到中学,不仅对学生是一个折磨,对老师也是一个折磨,这首诗几乎不可能按照通常理解诗的意义来理解。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岛,他这次香港诗歌节以后,带队去成都,据说那天爆满,北岛自己都讲简直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去日本。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谁都不懂,但是都在拥抱和热烈地谈论。他的讲座本来一个小时,结果讲了六个小时,然后天皇接见他的时候,沿途站满了人。他第二天早上站在宾馆阳台上呼吸东京的空气时,一看下边黑压压一片,把他给吓坏了,他说我怀疑我是个骗子,因为没有活着的人能享受这种尊敬和待遇和追捧。这是爱因斯坦以相对论受到大众追捧的时候,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
诗歌最迷人的地方是它的内蕴,内在对隐喻的理解。你可以把意义和大致的意思从英文翻到中文、法文,但你完全不可能把诗歌语音的内蕴,原封未动地或者哪怕是经过修改,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边。但是世界文学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化办法,就是把声音里边失去的转化为视觉呈现,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一贡献就是意象,这个在古诗里面是没有的。我们有的是诗如画画如诗,有画面感,但是意象是个内在的画面,内在的光。
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和平时代,而中国在时代转型。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泡沫的东西浮在精神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诗歌会是软绵绵的,会是带有消费性质。我有时候在北京,跟几个崇拜苏俄的诗人聊天,说起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他们在反斯大林的年代构成了一个崇高的信心。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现成的商品诗歌,这种崇高已经变成了消费,变成小资的消费对象,通过消费这种诗歌,来维持一种幻觉——我自动地是一个崇高者,这是一种假崇高。
按照朱大可先生的理论,中国现代诗歌全都是一个拷贝,是一个山寨,就连崇高感和诗歌里面来自苏俄的冷战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山寨。当然在普通意义上的阅读和写作之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批评。中国的当代诗歌批评是极其不称职的,因为诗歌写作中的很多东西是被批评的原创性给发明出来的,写作里面没有,阅读里面更没有,但是批评可以把这个没有给发明出来,而如果欠缺了这个发明精神,那么就算诗歌里面有的东西,也和没有一样。
八十年代,诗歌在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高处
徐鹏远:刚刚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不妨通过这一次的对谈,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建立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是对于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词语,不妨保持一份反省反思或者说警惕。就比如“大众”这个词,中国古代的汉语当中是没有大众这个说法的,中国有群的概念、有党的概念,是没有大众的概念,而且群的概念和党的概念,远远比我们现在的大众概念要小。而且大众所包含的人群里其实是复杂的,有许多的面相,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值得去分析。
那么到了今天,似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多元的时代,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地接触到我们历史当中遇到的那些具体的情景的相似的状态,我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和种类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代大众是不是真的需要诗歌,和我们那个历史时空比较,是不是真的更需要诗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题目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陷阱,我想听听两位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朱大可:“更”这个字确实像你讲的,是一个陷阱,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状态,因为你没有数据统计,现在大家都相信大数据的应用,凭什么说现在比五六年、六七年前更需要诗歌?
朦胧诗还真不是最大众的,最大众的时代,恰恰是八十年代第三代诗人崛起的时候,就是欧阳江河他们“第三代”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校园诗歌全面启动,一个诗人穿得破破烂烂,几个月不洗澡,就拿一本破诗集,在校园里每个寝室门敲过去,就会有人崇拜他、接待他,饭票一半都给他对吧,还睡同一张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可以混吃混喝,在全中国畅行无阻。
那个时候,在朗诵诗歌的时候,底下的女孩子跺着脚,涨红着脸,就跟看到港台和韩日歌星一模一样,我们的诗歌是在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这样一个高度,实际上是非常奇怪的状态。在那个时代,除了诗歌,青春荷尔蒙找不到其他出路。
回过来讲,还有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回到古典诗歌时代,唐诗宋词。唐诗宋词也未必就是大众化,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定性,那就是必须识字,而对于古代中国来讲,识字是一种特权,跟现代情况完全不同。文化是被垄断的,被极其有限的识字者、也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所垄断,他们毫无疑问是一个小众阶层,却统治了整个古典时代。所以我不太认为诗歌曾经在中国古代有过一个大众时期。当然口传是可以的,但你很难想想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农夫或农妇,会去背诵王维和杜甫的诗。
所以,诗歌成为相对大众的普及状态,只能是在二十世纪,这跟新的传播工具和教育方式有关。而且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的诗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现在大家都会缅怀那个年代。反正我个人是很缅怀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在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青春记忆、我们的挫折、我们的欢乐、我们的信念和理想,诗歌就这样忠实地伴随我们,成了我们灵魂深处的一部分。
现在我虽然不写诗,但隔一段时间总会去读诗,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激励。诗歌是语言的导师,是引领汉语的最重要的标杆,你能够从诗歌中获得那种语言的张力。诗歌是语言的力量源泉。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诗歌是寺庙,过段时间就要去朝拜一下。
对诗歌里青春骚动的需求说不定是中年产物
欧阳江河:这个“更”字我觉得可能不能成立,不光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八十年代是一个欣喜若狂的时代,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到今天是一个革命的第二日,有一个“节后综合症”。所以开始出现了一个诗歌减速并且散文化的状况,这个情况不光在读者身上,也发生在作者身上,比如近十年以来,北岛的诗写得很少,而文章写得很多,他在换转,按照当年茨维塔耶娃的说法“诗歌的速度太快了,这个车要翻掉了”,所以要换挡。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是在中年之后开始需要我们的青春意义上的诗歌,这个也是消费时代的疲软带来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个甚至让我想到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我们的诗歌意义上的这种需求,里面的青春的成分、骚动的东西,说不定是中年之后的产物,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吊诡,我们今天不可能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提出来,因为在诗歌的这个需要是一种成人的需要,一个怀乡病成人礼的回忆青春童年的需要呢,还是一个从来没有青春而在中年之后回到青春的需要,或者是提前消费?所以对诗歌的需要,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可老师说的“投影社会”,最后把自己也山寨了,也投到一个投射板里面,我们是影像、影子,我们的“道成肉身”的东西没有了,那个狠的东西、疼痛的东西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问诗歌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对诗歌的需要是不是对这些真东西的需要,我不知道,也可能我们是在对一个更虚假的、更山寨的一个假上帝的需要,我不知道。
超越一切时代的一流诗人根本不存在
提问:这个时代如果想做一个诗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诗人,诗人应该是男人中的男人、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谢谢!
欧阳江河:诗人跟性别的关系,我不怎么思考,把诗人从男人和女人中开除出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挺有意思。人类文明最苦恼的两个梦想,一个是飞翔,第二个就是男女同体。那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和你刚才讲的那个分类法暗和?
提问:今天这个讲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大众更需要诗歌”,我感觉没有抓住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是我们这个时代跟北岛那个时代的区别吗?北大的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教育是在培养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同样是北大的,另一个教授说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对我们的时代是个贡献。所以我在这里问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还有诗人怎么努力争取更多的大众?
朱大可:这位先生说得很好,你说让我们描述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真的没办法和你在这个地方讨论,否则我今天就回不了家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诗歌如何去争取它的大众。这个话题欧阳江河肯定是拒绝的,他不需要去争取大众,为什么诗歌一定要去争取大众呢?所以这个话题也应该做一个区分,就是有的诗歌它是可以去争取大众的,但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必须去争取大众,有的诗人就保持他的象牙塔状态不是挺好吗?让诗歌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比让诗歌只有一种状态要好得多。所以我想,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要让诗歌的生态变得更加自由、变得更加多样,而不是只有一种东西、一种标准,这样就会给不管是大众,还是中众,还是小众,或者是微众,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
欧阳江河:从诗人的角度,我引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诗,他说“我承认在一个二流的时代,我选择做一个二流的诗人,因为我是时代的忠实的臣民”。就是说诗人应该忠于他的时代,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只写优美诗歌和抒情诗的自我类型提纯,而不去面对内心之外的这个复杂盛世感到悲哀的原因。我不知道其他诗人怎么看,我一直认为我宁愿当一个忠实于这个时代的二流诗人,也不愿意当一个超越一切时代的一流诗人,因为那个超越一切时代的一流诗人,根本不存在。
“美”不是单纯的,也不是统治一切的皇冠
提问:中国的现代诗歌史上出现过新月派,闻一多先生提出过诗歌的三美理论,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但在今天,我总感觉整个诗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现代主义的、所谓朦胧派的诗歌。那么三美理论,对中国将来诗歌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欧阳江河:闻一多先生所说的“三美”,在他最有影响的诗里面,也是被偏离和纠正修改的。因为一个诗人写诗,不光是措词、形式问题,后面一定包含了很多时代精神、互文性、成长等等,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三美”可以概括的。不光是诗歌史,美术史、音乐史、电影史、建筑史所有的只要是跟创造性有关的东西都在变,经过整个20世纪人类的巨大努力,美本身的历史内涵也在变,美是什么,没有一个绝对的超历史的统一定义在那儿放着。那么既然连“美”本身都在改变修正,你能说这个“三美”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吗?不是,它是在写作过程中被发明、被修改出来的一种东西。伟大的诗人里尔克,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在重要的一首诗里表达过美可以轻易地毁了我们,却又不屑毁掉我们。现代性介入以后,连日本人自杀都选在了樱花季,不是说因为活不下去,而是美到不可能更美却又无法留住,为这个而死。美最后变成一个结束,变成一个自我毁灭的消失。美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诗歌怎么对待美?而且你认为的不美,恰好很可能是另一种的美。
保持小众是诗歌最健康的状态
徐鹏远:回到我们的题目,第二个陷阱,“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大众更需要诗歌”,当我们把大众和诗歌分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默认的是诗歌是一群精英写出来的精英文本,呈现给大众。很多参加文化活动的文艺青年,当他们思考、聆听的时候,是不愿意将自己划归为普遍理解的大众的。他们觉得自己最起码是迥异于大众的小众,即便他们可能还不敢把自己定义为精英,但至少透露出我们现在关于“大众”理解上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精英要俯下身去启蒙大众、去教育大众,或者说和大众分庭抗礼,大众的东西是一种样态,精英所创作的东西是另外一种样态;另一方面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大众会很反感这种论调,大众觉得脱离了大众,你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资格将大众视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平庸的或者说是缺乏思考的群体。那两位对大众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大可:江河刚才实际上是发表了一个反大众的宣言。诗歌要给你们什么?给的就是豹子的爪子,它是让人疼痛的东西,而不是给你骚痒的东西,不是文化口红涂抹在自己苍白的脸上。对这种态度我表示强烈的敬意。
我其实是个从诗歌批评领域逃到大众文化领域的逃跑者。为什么会放弃?大概在2001年前后吧,文学已经一片狼藉,左看右看,看不到什么好作品,没有办法,走上了大众文化研究的“邪路”,因为大众文化那时候刚冒出来几件很有意思的文本,一个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一个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都是大众文学的范本,意味着文学进入了大众消费层面。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刚刚出现,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在这时候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写了一些东西。同济大学成立文化批评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批评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学术机构,专门做这件事情,其中也包括对诗歌的外部景观,做一个更加细致的观察。
什么是大众?大众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大众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直到今天其实大众还有很大的程度是指打工仔。中国移动数字内容基地,曾经做过一个内部调查,他们的主要读者,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的民工,还加上销售代表和中学生,这些人最喜欢读的不是诗歌,而是魔幻、玄幻、武侠和言情,几乎全部都是垃圾,垃圾到了连编辑自己都受不了的程度。但当时的情况是,你越垃圾,你的读者量就越大。这就是中国大众读物的阶段性景观。
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得到改善,总体品质也在提高。流行的电视剧也一样,以前我们用央视机顶盒数据来进行统计,什么人在主宰电视的命运,是家庭妇女、退休的大妈,她们有时间坐在那里对着电视按下选择键,让有品位的好节目全部下野,剩下的全部是垃圾。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改变了呢?因为电视已经衰退,电视的广告商全部去投放数字平台,而这些的视频网站的观众,跟之前的观众完全不同,他们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看美剧,喜欢那些更加烧脑的东西。情况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整个格局颠倒倒过来了,要做电视大剧,必须先做网剧,网剧做完了再拿到电视台去播,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传播平台发生变化以后,整个收视观众的阶层也就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此反过来提升了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去年到今年连续出了几部电视剧,大家觉得不错的,分别是《红色》《伪装》和《琅琊榜》,这三部戏是去年到今年的重头戏,普遍被业界看好,而且正在成为今后电视剧的行业标准。
回到诗歌的话题,其实情况是一样的。诗歌经常处于一个阅读的精神分裂状态,要么就是极度精英的,要么就是极度大众的。当革命运动起来的时候,大众非常需要,因为革命理念的传播方式就是诗歌,在大跃进的时候,出现大量田头诗、黑板报诗、枪杆诗和快板诗,这些所谓的革命诗歌,像“撕片白云擦擦汗,凑近太阳吸袋烟”之类,充满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只有在那样一种疯狂的年代,诗歌才是最贴近大众的,但它其实是不正常的,是一种神经病状态。所以,过度渲染诗歌和大众的关系,和过于孤立诗歌和大众的关系,这两个方向都是危险的。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说法,中庸一点,诗歌是给小众看的,这比较正常,只是给大众写的诗歌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完全的孤芳自赏,完全的象牙塔,也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小众化是诗歌最健康的状态。
刚才江河说,诗歌有不同的品种,我这里讲的是一般常态,也有一些特别牛逼的诗歌,一般人就是看不懂,那也没办法。这样的诗歌我们也应该需要,就像金字塔一样,塔尖里有好东西,它在大众里所占面积最低,但它却有最高的高度。这是一个悖论:越好的东西,占有时间越长、占有高度越高,但是它影响的面积往往越小,而在金字塔底部的文本,恰恰是占有空间最大,但最没有高度和深度的,通常转瞬即逝、用完即扔。现在你们看图书市场,大家愿意看第二遍的书,应该说都算是好书。绝大多数图书看一遍扔了,那肯定是垃圾。这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评判标准。
什么是小众?小众又叫分众,小众分成很多需求,比如有一些小众喜欢国学,他们去参加各种总裁国学班,去听四书五经,领受孔子和孟子的教诲,还有一些人喜欢听中医养生,晚上还到广场上去跳一跳广场舞,也有人希望到基督堂去,唱一唱赞美诗,跟耶稣基督对话,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好,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慰藉自己心灵的独特的道路。
我赞同江河刚才讲的,文化一定是多元的,诗歌只是这个多元生态里的一部分。然后诗歌里边又有很多的样式和风格,可以任你去捡选。你是喜欢于坚韩东这样的口语诗呢,还是喜欢欧阳江河和臧棣这样知识分子诗歌,或者喜欢余秀华这样的诗,或者是汪国真同志的格言诗。当然,随着你的诗歌的这个鉴赏水平不断的提高,你自己会做一个选择,当你处于诗歌一年级的时候,你喜欢的可能是汪国真的诗,但是到了两三年级的时候你就不屑了,你就会喜欢更好一点的诗歌,像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然后你到了更高的段位时,你有可能会喜欢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喜欢更加形而上的,更具有终极关怀特征的,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心灵预设的结构,来进行诗歌阅读或者其它阅读,而且我也相信所有在座的朋友,你肯定不仅仅喜欢诗歌,还会喜欢其他的文学样式,这些互相叠加的文化套餐,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心灵提供自我慰藉、自我疗愈和自我改造的药剂。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诗歌究竟应该与大众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了。诗歌实际上跟大众就是彼此需要的关系,讲得尖刻一点,它就是一种消费和被消费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切东西都变成消费品,诗歌必然是各种消费品中的一种,诗集基本上是放在图书市场里销售的,它已经是一件商品,这个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当你去购买一本诗集的时候,就一定要花钱,每一本诗集的背后,无论是汪国真的诗歌还是江河的诗歌,都有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决定了它跟整个消费时代的关系。这个属性你是无法剔除的,但你可以在其间做更好的选择。通过像今天这样的讲座,我觉得江河讲得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仅需要那种能够用来抚慰我们的柔软药剂,我们也需要那种能够打击我们、刺伤我们的犀利的事物。
上海曾是全世界文青的避难所 今天只剩下小资
朱大可:我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异乡人,漂泊在我出生的土地上。为什么在我内心情感中,有跟这个城市非常融合的部分,也有跟它格格不入的地方呢?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上海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它在1927年到1937年曾经达到过高度自由的状态,它是全世界和全中国的文青避难所。所有精英都聚集到这里,吸纳、酝酿和创造各种思想。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开山之作《青年杂志》,还是文学中具有现代色彩的、能跟西方对接的、唤醒中国传统中的现代性幼苗的文本,都出现在上海。反叛的,先锋的,批判的,革命的,左翼的,右翼的,自由主义的、甚至是巴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传,语言相当的典雅优美。上海它什么都能掌握,真是一座伟大的森林。可是今天呢?你们看到了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小资。
上海是小资的策源地。90年代末开始,最早的小资诞生于上海,然后变成中产,慢慢地生长和扩展起来。什么叫小资?小资就是那种能够精细地消费的青年群体。什么叫精细消费?80年代人傻富傻富的,4000块买一件皮尔卡丹西装穿在身上,还是个土冒。小资绝不干这种事情,小资可以精细地消费,完成他个性的最完美的塑造,但是花的钱最少,这就叫小资。但是他只消费不创造。不创造是小资最大的软肋。
到了中产阶级阶段,你会发现事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今天写小说的主要作者群体是什么呢?是中产阶级太太,就是老公在全球五百强企业里当高管,她们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一手牵着狗绳,一手拿着写小说的笔,制造出某种我称之为“太太文学”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现状。所以今天你看,各省被评文学奖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批人,30到45岁以内的中年妇女,她们占领了中国文学的高地,这是事实。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文学就是因为闲暇才繁华起来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被教导,文学是一种苦难的产物,是社会黑暗、暴政和在底层挣扎的愤怒青年的战地。但是上海这个地方不可能,它只能诞生这种中产阶级的太太文学,不仅上海,广州、南京、杭州这样一些城市,尤其是在南方,文学就在胡兰成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八个字的笼罩下诞生的,当然诗歌是另外八个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我没有任何嘲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它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我非常赞同江河刚才说的,我们也渴望看到另外一个侧面,听到一种更暴力、更粗野、更不和谐的声音。所以在这里我会有一个期待,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期待,在一个前所未有和剧烈变动的社会语境中,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我们都期待文学有一个剧烈的变化,期待一种伟大的革命性文本的诞生。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文化先锋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未经授权,不得转载。